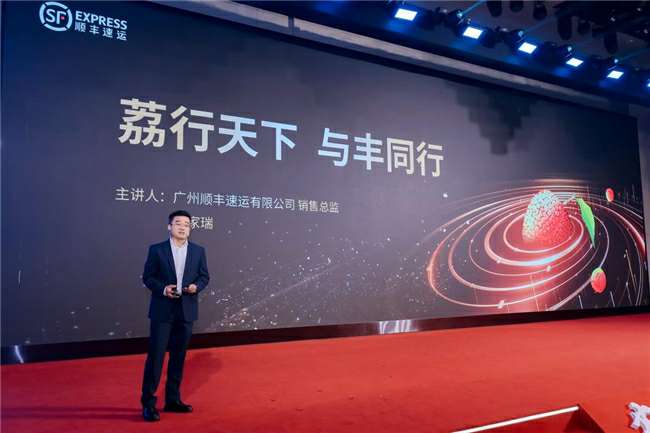“魔法打敗魔法”不是解決問(wèn)題“達(dá)摩克利斯之劍”
1月27日,有網(wǎng)友在社交媒體上發(fā)文稱(chēng),坐火車(chē)時(shí),對(duì)面的小孩一直尖聲吵鬧,還多次踩到或踢到自己。在與孩子的家長(zhǎng)溝通未取得效果后,該網(wǎng)友突然“發(fā)起了瘋”:學(xué)狗叫、大聲唱歌、捂頭尖叫、一會(huì)兒笑一會(huì)兒哭……結(jié)果孩子家長(zhǎng)“嚇得不行”,捂著小孩的嘴立馬走開(kāi),整列車(chē)廂都安靜了。
這段“魔幻”的經(jīng)歷,在網(wǎng)上引起了網(wǎng)友們激烈的討論,不少人都大喊“過(guò)癮”,認(rèn)為這是“用魔法打敗了魔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大快人心。持反對(duì)意見(jiàn)的網(wǎng)友認(rèn)為這是“以暴制暴”,與小孩的“發(fā)瘋”并無(wú)區(qū)別,并不是成人成熟的處理方式。那么“魔法”是解決問(wèn)題的“達(dá)摩克利斯之劍”嗎?用這種相對(duì)極端卻立竿見(jiàn)影的處理方式來(lái)維護(hù)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值得提倡嗎?我看未必。
首先,這些“魔法”看似“行俠仗義,除暴安良”,讓不遵守社會(huì)公約的人受到遭受同樣的方式打擊,但這種方式無(wú)疑于把不文明行為重新演繹了一遍,除了讓當(dāng)事人受到刺激外,其他旅客也同樣會(huì)再次受到影響和驚擾。看似“大快人心”的結(jié)局背后,未必在法律法規(guī)上能站得住腳。如果對(duì)方并不接受這種方式,甚至可能造成矛盾升級(jí),引發(fā)更嚴(yán)重的沖突。
其次,用“魔法打敗魔法”并不是人們處理問(wèn)題的初衷,如果“熊孩子”的家長(zhǎng)能夠及時(shí)出面進(jìn)行制止,干預(yù),事情就會(huì)向好的方向發(fā)展,但往往事情失控的原因都是大部分“熊孩子”的背后都存在“熊家長(zhǎng)”,“熊家長(zhǎng)”的不作為甚至包庇縱容是沖突加劇的主要原因。縱觀過(guò)往案例,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當(dāng)不文明行為發(fā)生時(shí),訴諸“官方渠道”往往不能起到立竿見(jiàn)影的效果,特別是對(duì)于一些自以為是的“熊家長(zhǎng)”,甚至“理直氣壯”胡攪蠻纏,面對(duì)這種情況“魔法”的出現(xiàn)似乎就順理成章了。但正常人不應(yīng)該突然“發(fā)瘋”,智慧和勇氣也不應(yīng)該浪費(fèi)在阻止大聲喧嘩、脫鞋、霸座這樣的事情上。如果,在公共空間里,大家都能夠遵守社會(huì)公約,給予他人和自己充分的尊重,考慮自己權(quán)益的同時(shí),也考慮他人,那么類(lèi)似的“魔法打敗魔法”的雙輸現(xiàn)象就應(yīng)該大幅度減少,甚至銷(xiāo)聲匿跡。
近幾年,關(guān)于公共空間文明與秩序的討論愈發(fā)受到關(guān)注,這說(shuō)明人們對(duì)社會(huì)文明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經(jīng)過(guò)一次次的圍觀和討論,我們可喜地看到事情也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比如,旅客外出乘坐高鐵、飛機(jī)時(shí)開(kāi)始做更多準(zhǔn)備,來(lái)應(yīng)對(duì)旅途中的各種需要;鐵路部門(mén)開(kāi)始在多趟列車(chē)上提供“靜音車(chē)廂”服務(wù),推出《鐵路旅客文明出行倡議》,對(duì)于個(gè)別旅客的不文明行為隨時(shí)進(jìn)行提醒和糾正,而面對(duì)一些不聽(tīng)規(guī)勸,肆意妄為的“害群之馬”,出手也越來(lái)越果斷及時(shí),懲罰力度不斷加大。文明出行、懂禮貌、做有素質(zhì)的國(guó)民,越來(lái)越多人形成了這樣的共識(shí)并且在努力踐行。
盡管有行為習(xí)慣、文化差異存在,人與人之間的標(biāo)準(zhǔn)不盡相同,但只要設(shè)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遵守社會(huì)公約、不影響他人、特殊情況下盡量減少對(duì)他人的妨礙,相信總能找到“平衡點(diǎn)”,也會(huì)很好地被別人接受和理解。“魔法”或許不該被鼓勵(lì),但由此引發(fā)的思考和行動(dòng)價(jià)值得我們深思和商榷。(趙志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