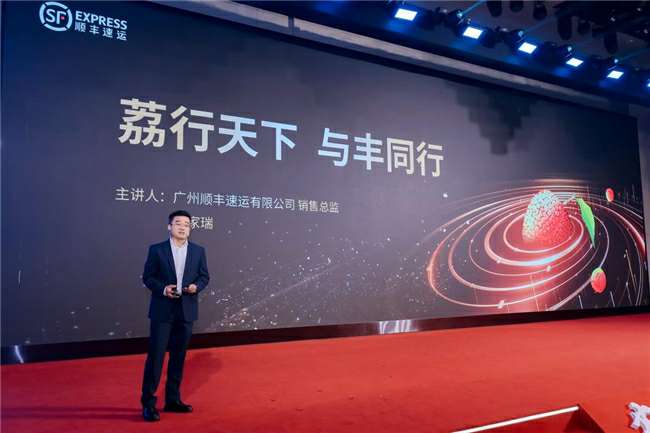地“活”,村興——安徽農村改革新觀察
“當年貼著身家性命干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志。”
安徽是農村改革發源地。45年前,正是在這樣的隆冬時節,安徽開啟農村改革序幕。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強調,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親臨安徽考察。大灣村、小崗村、淮河蒙洼蓄洪區,是總書記實地考察調研的安徽鄉村。
如今,歷經16次蓄洪的淮河最大蓄洪區掙脫了“民生洼地”的境遇;大別山革命老區的深山遠村一派人旺業興景象;而在“改革第一村”小崗村,“地”里下著一盤更大的棋,承載著全新的前行探索。
農村改革是“三農”發展的重要動力,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法寶。這三地村情差異巨大,資源稟賦各異、發展階段不盡相同。他們的改革措施和發展路子也各具特色,但都被實踐證明是促進鄉村全面振興行之有效的路徑。
那么,他們正在經歷的滄桑巨變中蘊含著怎么樣的改革邏輯?
連日來,深入這三地調研采訪,在撲面而來的鄉村振興新氣象中,更加深刻感受到,繼續把住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這條主線,把強化集體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實現農民集體成員權利同激活資源要素統一起來,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農民愿望、保障農民利益的新路子,就像一根充滿“魔性”的杠桿,正在撬動起鄉村全面振興的大變局。
土地是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地“活”,村興,奏響著新時代新征程上的農村改革交響。
“麻糊地”也香了
——蒙洼蓄洪區人、水、地“復雜三角”何以解扣
今年是蒙洼蓄洪區建成70周年。
據記載,歷史上的蒙洼是地廣人稀的湖洼地,分布著8個長年的積水湖,野鴨成群,是捕魚的“戰場”,本是淮河干流中游蓄滯淮河洪水的場所。
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冬天,阜陽專區治淮指揮部按照“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動員阜陽、潁上、臨泉、阜南4個縣的30萬民工,開始建設蒙洼蓄洪區。1953年1月王家壩閘動工興建,當年7月竣工,這也標志著蒙洼蓄洪區正式建成啟用。
當時這片180平方公里的蓄洪區內生活著5.4萬人。如今,這里4個鄉鎮的人口達到19.5萬人,耕地面積19.8萬畝,其中還有大量人口生活在131座莊臺上。
人水爭地,一直是蒙洼蓄洪區的主要矛盾。70年來,先后16次蓄洪,成為新中國運用最頻繁的蓄洪區。很長一段時期,當地老百姓流傳的說法是,全部家當系在一條繩子上,洪水一來,拎起來就走。
蒙洼蓄洪區因為頻繁蓄洪,耕地肥沃,同時地勢平整,耕作條件也好。
但這種地力上的優勢不足以覆蓋洪水頻繁襲擾的破壞性損失。同時,蓄洪區內也不能布局工業項目和永久性設施農業等項目。幾年前,中央相關部門負責同志來這里調研時,時任安徽省負責同志在匯報中說:“這里才是真正的‘民生鍋底’。”
人、水、地的“復雜三角”何解?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考察時強調,要根據蓄洪區特點安排群眾生產生活,揚長避短,同時引導和鼓勵鄉親們逐步搬離出去,確保蓄洪區人口不再增多。
一間移動的特殊辦公房,體現著這里揚長避短的智慧。
這間辦公房位于王家壩鎮,這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居然是帶輪子可移動的“房車”。平日里,里面可以辦公,洪水一來,推著就能走,靈活機動。房子的主人叫任超,是當地的芡實種植大戶。
蓄洪區里有一些低洼地,原本都已拋荒了,因為下雨時易澇、干旱時易裂,當地農民稱之為“麻糊(當地一種糊狀特色湯羹)地”,都不愿種。任超有頭腦也有闖勁,他從當地農民手里流轉了500多畝地,將部分低洼地平整后實行“小麥+芡實”輪種,收獲時節還雇了50多位當地工人幫忙,芡實主要銷往江蘇、浙江一帶,行情還不錯,幾樣農作物輪作下來每年能掙幾十萬元。
連“麻糊地”也香了,因為找對了路子。這條路子被阜南縣副縣長王傳力稱為“發展與水共生的適應性產業”。同時,也因為找到了愿意種并且能種好的人。
同樣一塊地,通過“適度規模經營+適應性產業”的組合拳,就從拋荒狀態完全“盤活”,產生了可觀的增值收益,由此實現“三贏”:大戶實現規模化種植,得了經濟效益;農戶得了土地流轉金,還能進合作社打工掙錢;當地發展了產業,地方政府增加了稅收。
其根本在于,因地制宜地把握了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改革主線,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重組人地關系,激活農業生產中土地、人力、投入等要素資源,由此催生了土地收益的成倍增加。
在蒙洼蓄洪區,這樣的探索和實踐尤為重要。
農業,是三次產業中的“弱質產業”,在蒙洼,這種特性被放大到更高風險層級。因為一次蓄洪,個體農戶多年源于種地的收益積累可能一朝就不復存在。
揚長避短、破解難題,首要的就是放大源于土地的收益,使之一定程度上能夠逐步覆蓋蓄洪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進而支撐農民增收。
習近平總書記3年多前考察的西田坡莊臺,位于蒙洼蓄洪區曹集鎮利民村。
如今,這個村已經流轉土地2500畝,推行“農業大托管”2000畝。“下一步,通過‘農業大托管’交由專業農場進行精細化耕作,預計小麥畝均增產100斤,實現農田增量、增產、增效。”阜南縣曹集鎮利民村村支書李敏說。
適度規模化經營促進土地收益增值,適應性產業的發展則讓土地增值更具確定性、持續性。
如今,在蓄洪區內,已經形成水生蔬菜、生態種養、水禽養殖等多條“水生產業帶”,并重點推廣應用稻蝦(漁)連作、藕漁共生等農牧漁結合模式,以蓮藕、芡實為主的水生蔬菜面積達4.5萬畝,稻漁綜合種養面積達2.8萬畝。
土地收益的增值,讓一部分農民不種地也能獲取種植收益,逐步擺脫“靠天收、看洪水臉色”的境遇,是真正的“避短”路子。
不種地的農民干啥去?
張朝玲夫婦如今在蒙洼蓄洪區乃至整個阜南縣都很有名。夫妻倆在當地創辦的安徽德潤工藝品有限公司,把由杞柳制作的各種工藝品賣到海外,出口到歐美37個國家。
杞柳是一種近水植物,即使連續20天泡在水中也不會腐壞,所以可以在蓄洪區內大面積生長。杞柳能編織成各樣的藝術品和生活用品,包括果籃、家具、裝飾品等。
張朝玲說,在這里辦廠,不僅原料豐富,質優價廉,會做柳編的人也多,在家里就能干。只要派人將模型送給農戶,他們在家里就能完成。這樣,就帶動了當地100多戶農民就業。
蓄洪區內不能布局工業項目,但蓄洪區的保莊圩內可以,這個用圩堤保護起來的安全區域就是用來布局當地群眾所需要的各類生產生活設施的。
不用種地的農民,在這里有很好的去處:可以把家搬到這里,可以在這里務工掙錢。
于是,保莊圩里發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制箱包、織柳編、做服裝……這些廠充分吸納了當地人就業,人們不用出門打工,在家門口就能上班,還能照顧家庭。
在紅亮箱包有限公司里,王敏老人正認真地做“翻包”的活。攤開皮包、翻好整理好就是他每天要做的事,一個月2000多元的收入讓他挺滿足。“我已經一大把年紀了,現在上班又近、掙錢還不錯,這工作我很滿意。”王敏笑稱自己是廠里“元老”,已經干了10年了。如今,這家企業已經有150多人,產值1000多萬元。
“你看,那邊是我們正在建的新車間,以后規模會越做越大。”紅亮箱包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恒亮開心地說。
像紅亮箱包這樣的企業不在少數。截至目前,蒙洼蓄洪區小微企業數達到75家,年產值突破12億元;其中規模企業達到17家,前三季度規模工業產值達到4億元,同比增長20%,解決4000多人就業。
不用種地的農民,成了蓄洪區的“長處”,成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力優勢。
把住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改革主線,揚長避短,就解開了“人、地、水”關系的“結”:土地這一端,以規模化發展的適應性水生產業來擴大增值收益。農民這一端,以與土地“解綁”的人力優勢來布局勞動密集型產業。以此為支撐,引導和鼓勵鄉親們逐步搬離蓄洪庫區,“人為水讓路,水給人出路”,進而走向人水和諧。
蓄洪區各類資源要素正持續被激活,由此邁上鄉村全面振興的前行之路。
這也給了當地干部信心和底氣。
“人家的很多好做法,我們很難學得了,蓄洪區的產業發展關鍵是要適合自己。因地制宜,是我們發展最重要的經驗。”王傳力說。
“多業態”紅火了
——大灣村的“村有產業、戶有收益”之路何以走通
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千差萬別的鄉情村情,始終是深化農村改革、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最復雜所在。
從傍水而居的蒙洼蓄洪區向南約200公里,進入群山連綿的大別山革命老區,就來到群山環抱的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
金寨縣的縣情介紹中總會有這句話:集老區、庫區、高寒山區于一體。而大灣村就處于所謂的“高寒山區”,山高谷深,群山阻隔,很難想象能被“焐熱”。
老區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掛念在心。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大灣村脫貧工作,了解茶園、魚塘、小型光伏電站等扶貧項目的生產經營、成本收益等情況,并同村民們進行親切交流。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特別是不能忘了老區。
脫貧后的深山遠村里,處處是笑臉。
“以前哪能想到現在的生活這么好,我是大灣村發展變化的受益者。”大灣村“喜來山莊”店主閔玲的盈盈笑意,與她經營的這家農家樂店名一樣,透著滿意與喜悅。
說這話時,她正忙著準備游客提前預訂的飯菜。2017年之前,她和丈夫一直在上海打工。那一年,她很直觀感受到老家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于是回到村里經營起了農家樂和民宿。“以前誰都不看好我搞農家樂,當時還欠債幾十萬元,現在不僅債都還清了,一年收入還有20多萬元。”
閔玲沒說虛話,他們兩口子生活變好,直接得益于大灣村依托紅色文化和綠色資源,走了一條紅綠結合、茶旅融合的產業振興路子,進而帶動不少村民吃上“旅游飯”。
“2022年大灣村接待游客35萬余人次,旅游綜合收入5000多萬元。”大灣村黨總支第一書記余靜說,“村有產業、戶有收益”的產業格局正在形成。
村與戶關系的背后,是當地把住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這條主線,強化集體所有制根基的生動實踐。
深山農村發展之難,除了地理條件限制之外,耕地少,可利用的土地資源緊缺也是一大根源。當年大灣村的扶貧產業先是選擇在茶園、魚塘、小型光伏電站上用力,也正因為用地少、易突破。
很快,當地就找到了做活土地文章、盤活土地資源的路子。
如今,在大灣村里,作為搬遷安置點的一棟棟白墻灰瓦的二層小樓整齊排列,與村里的老房子隔溪相望。
“我們將宅基地制度改革與易地扶貧搬遷等政策相結合,把政策疊加效應很好地發揮出來了。”大灣村黨總支書記何家枝說,大灣村從2016年開始啟動易地扶貧搬遷,先后建成4個易地扶貧安置點,近130戶人家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并搬遷到安置點,騰退的宅基地全部復墾為耕地。
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穩住神、把好方向,關鍵是絕不能損害農民利益。
74歲的村民汪能保說,他享受到易地扶貧搬遷補助和宅基地騰退補貼,搬到了老宅對面的新房。家里通了自來水,還擁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這在以前想都想不到”。
通過騰退宅基地復墾等辦法,大灣村盤活了“沉睡”的土地資源,找到了激活要素資源、強化集體經濟根基的“杠桿支點”。
金寨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負責人介紹,從2021年起,金寨縣啟動大灣村“多規合一”實用性村莊規劃編制,統籌資源,優化用地布局,保障產業發展用地空間。根據“要素跟著項目走”的原則,3年來,大灣村累計新增建設用地70多畝,這也為大灣村農產品加工、茶旅融合等一批項目提供了用地保障。
就山區村現狀而言,盤活的土地資源,率先用于突破壯大村集體經濟的產業項目,由此帶動更多外部產業資源注入,以“村有產業”帶動“戶有收益”,大灣村蹚出的是一條具有可復制性的興村富民路子。
冬日里,大灣村的旅游熱點項目“大灣十里漂流”暫時冷清下來,但這里的負責人王昭依舊每日駐守在游客中心,做一些日常維護工作,靜待來年夏季“開工”后收獲更旺的人氣和財氣。
“大灣十里漂流”是大灣村集體經濟的重要產業項目,2020年8月投入運營。大灣村通過自然資源入股項目,按照漂流門票收入的40%參與分紅。去年大灣村207.7萬元的集體經濟收入,這個項目就貢獻了約100萬元的收入。
除了增加集體經濟收入,更重要的是,這個項目帶火了人氣,豐富了當地旅游業態,帶動村民們的農家樂、民宿等生意也熱起來了,活躍整個村的產業氛圍。
“漂流游玩高峰期,我們用工規模在100多人,基本是本地人,帶動了就業,幫助老百姓增加收入。”王昭說。
在大灣村的農特產品展銷中心,各種特色農副產品琳瑯滿目,旁邊的車間內還有工人們在加工和包裝小香薯。
“這個項目也有大灣村集體經濟參與。”花石鄉黨委副書記蔡志彪說,大灣村爭取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500萬元的投入,建設大灣農特產品展銷中心。以此為平臺,引進一家縣內企業來這里創辦大灣生態農業有限公司,發展小香薯與南瓜生態基地建設、加工與銷售,帶動農戶發展小香薯和南瓜種植500余畝,通過產品加工、展示銷售、餐飲體驗,提供穩定就業崗位100余個。
這里的大多農戶是茶農。茶產業成了大灣打通“村有產業”帶動“戶有收益”路徑的著力重點。
茶葉銷售是難題。2017年,金寨縣利用財政整合資金建設大灣茶廠,引進安徽蝠牌茶業有限公司來運營,為400余戶茶農們提供穩定銷路,也提供了一部分務工崗位。2022年,大灣蝠牌茶廠實現銷售額420余萬元。在此過程中,大灣村也通過茶廠的租金,增加了集體經濟收入。
資金入股、資產租賃、收益分紅……記者在大灣村實地走訪調查6個村民組看到,“村有產業”正在通過多種方法促進著“戶有收益”。
“我們沒辦法學其他平原區鄉村,可以搞鄉村產業規模化、集群化。”蔡志彪說,大山里的村莊,還是要順應自然稟賦,從“小而精”的方式入手,用多元業態產生廣泛收益。
滴水可折光。特色種養、旅游民宿、光伏電站……大灣村的多元業態熱起來了,村里農民的年人均收入也由2016年的7120元增長為2022年的17038元。
強化集體經濟之基,以此激活鄉村產業發展各類資源要素,讓農戶分享更多改革成果。鄉村全面振興之路上,大灣村的動力活力正在持續涌流。
“種地人”年輕了
——小崗村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路何以走寬
村外,平疇沃野。村旁,廠房成行。
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以越來越不同的“氣場”展示著獨特的存在,成為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農村新變化的一扇櫥窗。
記者12月下旬來到這里時,正值寒潮襲來,氣溫驟降。冷風寒雨中,更勾起對45年前寒冷冬夜里18戶農民按下紅手印的那種勇敢與決絕的追憶。
但田野里,冬小麥已經吐出了新綠,一望無際。
我國農村改革是從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開啟的。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考察并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總書記強調,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這是農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創新。
近年來,小崗村緊緊圍繞處理好農民與土地關系這條主線,穩步推進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全面完成2.2萬畝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1.37萬畝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頒證,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讓每一塊土地有了“身份證”。
此舉讓農民吃了“定心丸”,不僅給持續做活土地文章拓展了更大空間,也給“農民和土地”這一對關系帶來了新的生機和變化。
34歲的周地帥說不清當初為什么要給自己取這個名字,但如今看來,與小崗村的現狀以及他自己所做的事倒還比較貼合。
在種糧大戶程夕兵的農機大院,播種機、插秧機、收割機……各式各樣的農用機械擺滿院落。今年60歲的老程,把這六七十臺農機交給女婿周地帥來打理了。
周地帥原先在鎮上一家企業上班,看到岳父年紀大了,一個人種田辛苦,便辭掉了工作回鄉干起了農業,經過幾年在農田里摔打,小周現在各種農機操作自如。
小崗村地處江淮分水嶺,以崗地為主,土地散碎,耕作條件差。“一塊地就三五分大小,成畝的地都少,田里沒有像樣的路,農機進出不方便,地不好種。”周地帥說。
“三權分置”下,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承包權益與承包地塊不再直接掛鉤,為高標準農田改造提供了制度支撐。這幾年,小崗村順勢而為,全部完成了高標準農田改造,基本實現高標準農田全域覆蓋,先后實施了“引水上崗”“引淮潤崗”等農田水利項目,破解了崗地用水難題,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善。
今年夏季,小崗村的小麥喜獲豐收,平均畝產超過800斤,比丘陵地帶正常的單產高出近200斤。
連片的高標準農田適宜機械化耕作,種起來不僅省心省力,還能節約成本,增加效益。所以,像周地帥這樣的年輕人才愿意回村來種地。
“種地實現機械化以后,人工成本至少節省一半,比如以前靠人工插秧,我這600畝水田要請20個人插秧,一天也不過干20畝,一季下來光工人工資就十幾萬元,現在換成了機插秧,兩三個人就夠了,一天能完成三四十畝,成本大大減少。像噴灑農藥,以前靠人工噴灑,一天也就二三十畝,現在無人機噴灑,六七百畝連片的農田一天就能完成。”
這個種地的年輕人,“小算盤”打得叮當響。
土地確權后,農民都愿意把地流轉出去。小田變成大田、低產田變成高產田后,種糧大戶愿意流轉更多的地來種。就這樣,周地帥和岳父種的地,從最初的100多畝增加到現在的700多畝。
種更多的地,有更大的奔頭。“以前種地辛苦還不賺錢,現在土地耕作條件改善,糧價也比較穩定,種地有錢賺。”周地帥說,這兩年他家種地收入每年都在二三十萬元。今年糧食喜獲豐收,收入差不多能在四五十萬元。
地的收益成倍放大了,種地的人也更加年輕了。“誰來種地”的難題,在小崗村也在破題。
這就是制度創新的“魔力”。
“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村的一切都是源于此。”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李錦柱說,從小崗村的實踐來看,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鞏固了所有權,穩定了承包權,搞活了經營權。目前,全村土地流轉率已達74%,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31家。
搞活經營權,也拓寬了農村集體資源資產增值的路子,壯大了小崗村的集體經濟。2022年小崗村集體經濟收入達1300萬元。自2018年起,小崗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連續6年為村民累計分紅超1400萬元。
如今,小崗村村民基本上都住進了統一規劃建設的居民小區,上下兩層半的小洋樓,帶院子和廚房衛生間,水、電、氣、網等基本生活設施配套完善。
“我們不是拿國家的財政資金改變自己的面貌,而是利用了國家土地‘增減掛’的政策,把空心化的散亂村莊進行了整合,復墾成耕地。不僅置換出1000多畝的建設用地指標,也徹底改善了村民生產生活條件。”李錦柱說。
搞好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權利分置和權能完善,讓廣大農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探索。
通過充分搞活經營權,村民持續分享到更大的收益和成果,小崗村“三權分置”改革的路子持續走寬。
土地盤活了,農業農村的各類資源要素也相應被激活。小崗村設施農業、農產品深加工企業蔚然興起。
在小崗凱盛智慧農業有限公司的溫室大棚里,一排排無土栽培的番茄郁郁蔥蔥,紅彤彤的小番茄像鈴鐺一樣密集掛滿枝頭。
1998年出生的企業種植主管吳少魏介紹,這種無土栽培的水果番茄不僅口感好,而且產量高,普通番茄只能結6穗到8穗果,而這種番茄可以結35穗果子,采摘期長達八九個月,產量是普通番茄的5倍,價格也要高出許多。
他大致算了筆賬:“設施大棚每平方米番茄產量可以達25公斤,畝均產值可達40萬元,達到了城市里工業用地的產出標準了。”因為收入穩定,公司吸引了80多人來這里就業,不少都是像他這樣的年輕人。
地能來種,班能來上。返鄉就業的,外來創業的,小崗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帶來了青春的氣息,更帶來了振興的希望。
“小崗的根在農業,農業的根在土地。我們突出的感受就是,土地活,則農業興、鄉村旺。”說到這里,李錦柱感觸良多。
“小崗夢也是廣大農民的夢”。深化農村改革,始終是逐夢路上的強勁“引擎”。
撰稿:記者 胡旭 王弘毅 范克龍 許昊杰